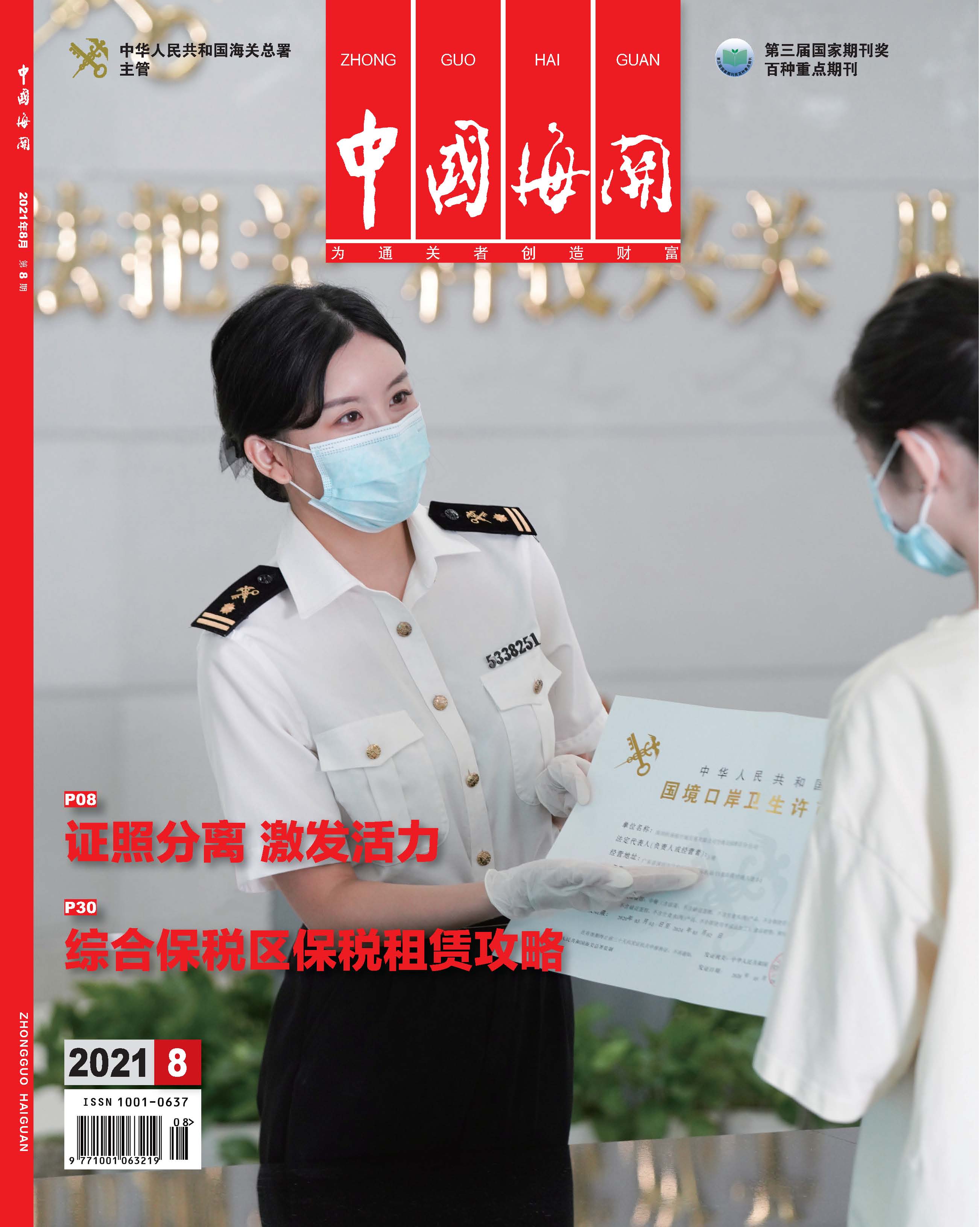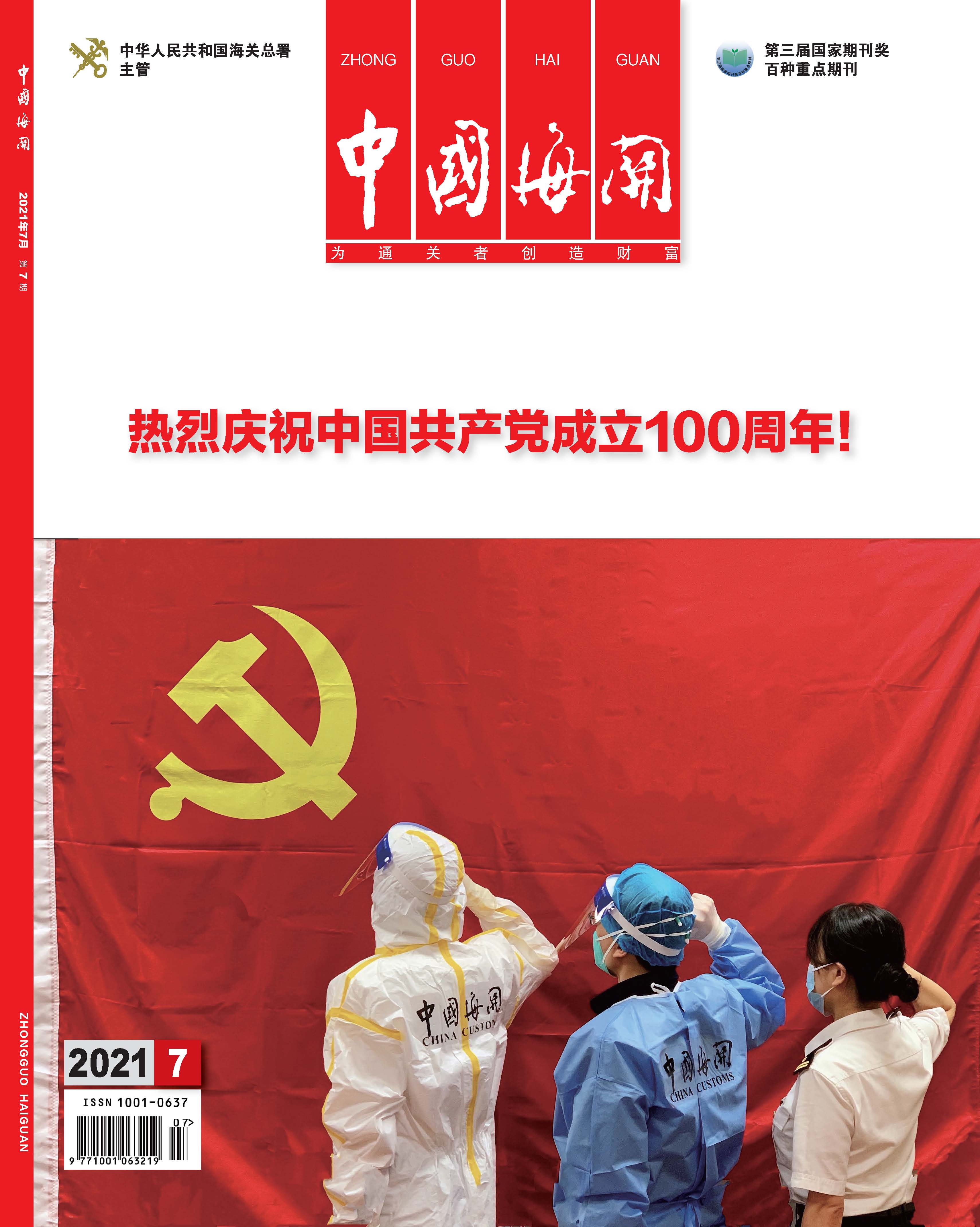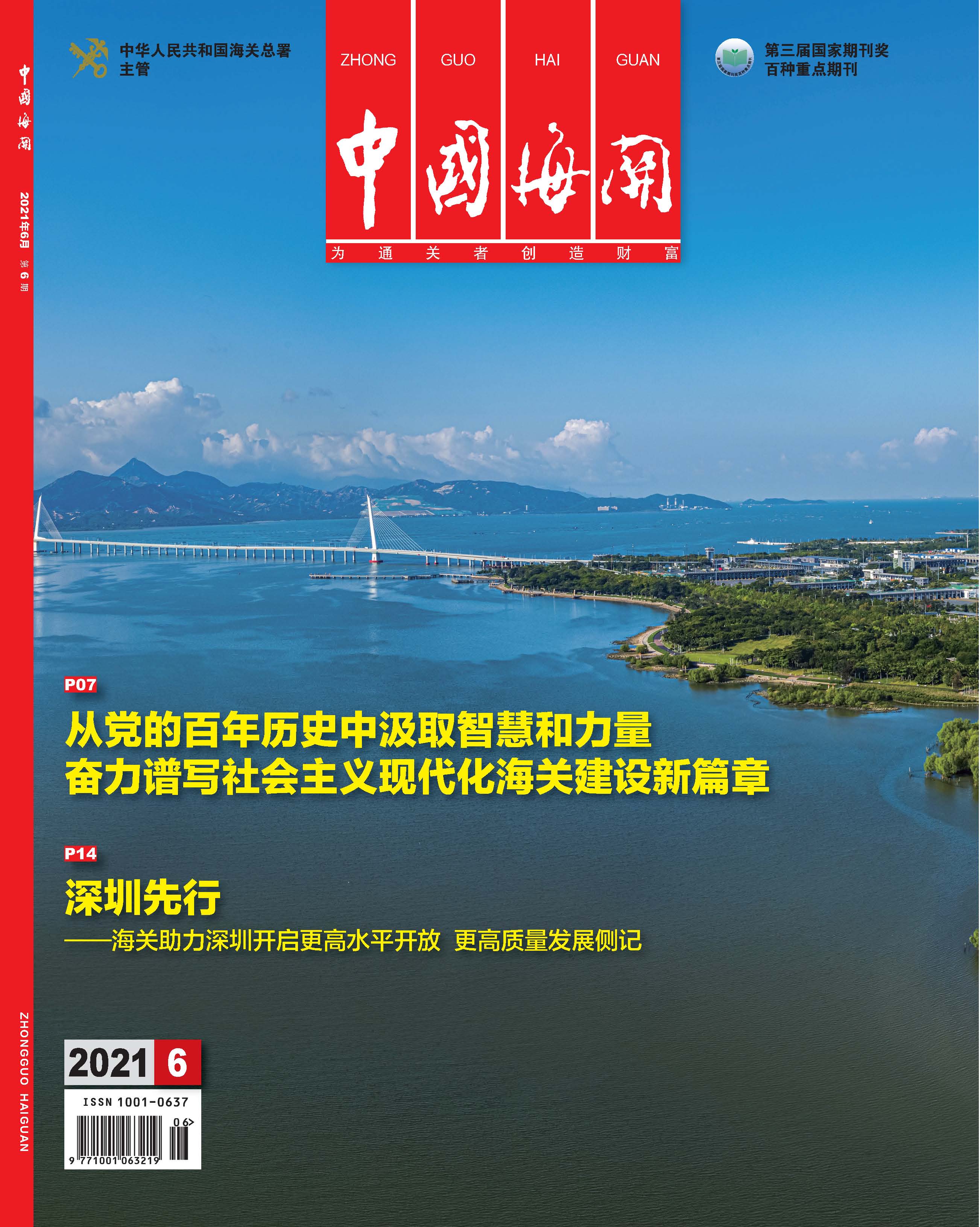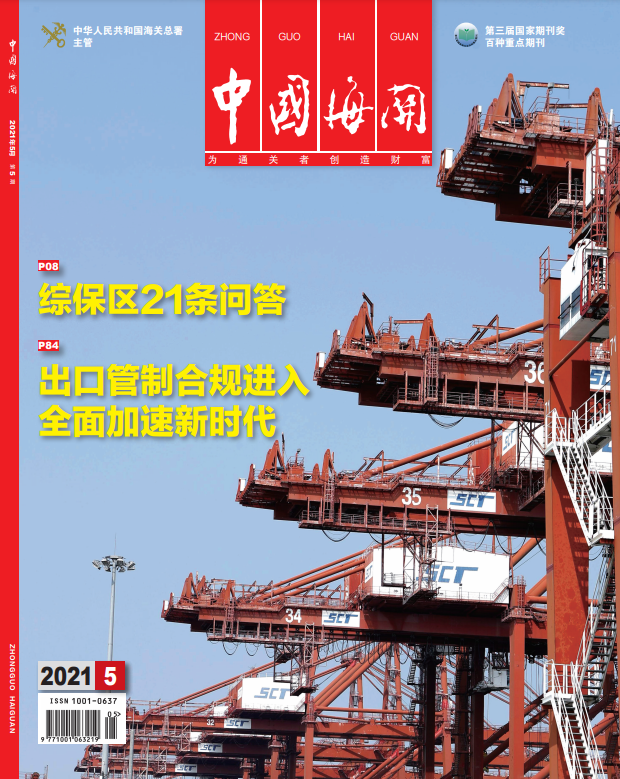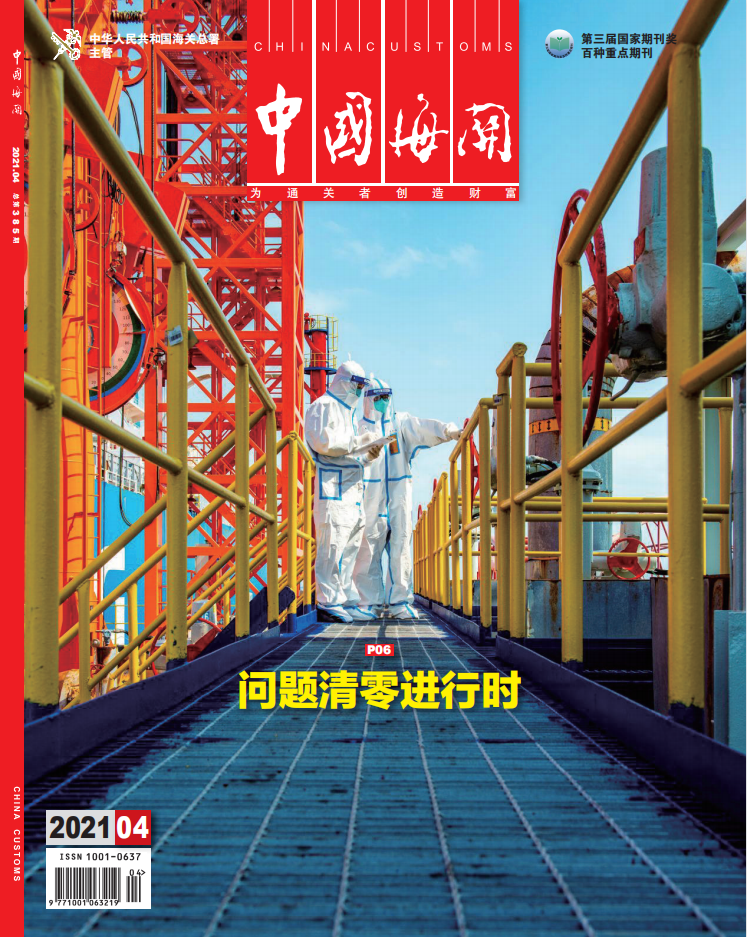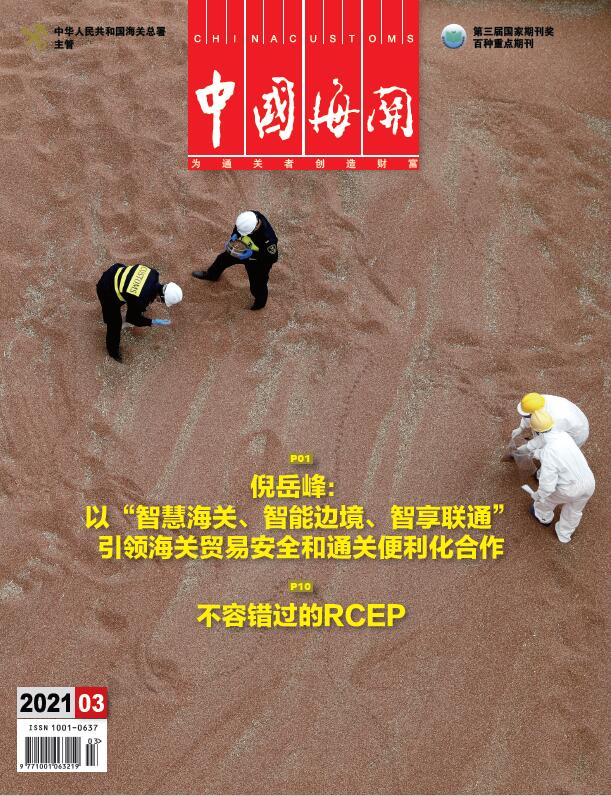CopyRight 2009-2020 ©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 中国海关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从欧盟对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 看欧盟的反规避制度
文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马荣花 赵晶
对规避行为如何认定?
通过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发起的两起反规避调查中,可看出欧盟对规避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一:
2012年9月25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并于2013年5月29日做出肯定性终裁,决定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的反倾销税延展至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进口的涉案产品。
案例二:
2014年9月2日,欧盟委员会又决定对中国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并于2015年5月18日做出肯定性终裁,决定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的反倾销税延展至自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进口的涉案产品。
从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来看,欧盟委员会认定规避成立的条件主要包括下列内容:贸易模式的变化、规避行为的性质、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缺乏正当的理由或经济上的合理性、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被破坏、存在倾销的证据。
贸易模式的变化
贸易模式的变化是欧盟认定规避行为是否存在的首要条件。欧盟委员会对自行车发起的这两次调查是针对转运和组装这两种规避形式。通过对这两次调查的裁决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委员会认定贸易模式是否发生变化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的:首先,从中国和第三国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的数量是否发生大幅变化;其次,从中国出口到第三国的自行车的数量是否发生大幅变化;最后,自行车的产量是否发生大幅变化。
以案例一为例,欧盟委员会认定,从2005年7月反倾销税增加到48.5%以后,200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的自行车与上一年度相比下降38.2%,此后就逐年下降,整个调查期内,中国到欧盟的自行车下降了80%。同时,从印度尼西亚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则从2005年开始增加,甚至在2006年的出口是2004年的两倍,除了在2009年有轻微下降以外,一直持续增长,在整个调查期内,从印度尼西亚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增长了157%。从马来西亚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在2005年之前微不足道,但是在2005年则急速增加(2005年的出口量是2004年的21倍),整个调查期内,从马来西亚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增加了1623%。从斯里兰卡和突尼斯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整个调查期内,从斯里兰卡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增加了282%,而从突尼斯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增加了200.3%。
上述期间内,从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自行车则明显增多。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自行车从2008年开始增加(与2004年相比增长56.2%),此后一直到调查期结束,除了2009年有轻微下降外,一直在增长。整个调查期内,从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自行车增长了83.8%。而调查期内,从中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自行车增长了99.6%;从中国出口到斯里兰卡的自行车增长了132.5%;从中国出口到突尼斯的自行车更是从调查期初(2014年)可忽略不计的2534辆增加到170772辆(增加了66.4倍)
关于配合调查的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公司的产量,在调查期内分别增加了54%和24%,而斯里兰卡公司的产量则有轻微下降;唯一一家配合调查的马来西亚公司2010年才开始生产和出口自行车,由于没有其他公司配合调查,所以无法获得马来西亚生产自行车的真实产量。
综上所述,在2005年7月反倾销税增加以后,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减少,而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增加,并且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自行车增加,因此构成了贸易模式的变化。
规避行为的性质
在确定贸易模式发生变化以后,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贸易模式的变化是否是反规避条款中规定的规避行为所导致。在案例一的裁决中,欧盟委员会认定是通过第三国转运和组装的方式规避反倾销调查。
◎对于转运的规避行为,在本案中,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公司,欧盟委员会认定存在转运的规避形式,理由是:该公司提交的数据无法核实,因为公司声明其并不保留报告豁免表(Exemption form)中数据的工作底稿,因此公司无法解释并说明如何获得其填报的数据。而且,公司提交的数据不具有可信性,因为报告数据所使用的财务记录是不准确的(例如采购和生产数量等)。此外,调查还发现该印度尼西亚公司的销售经理同时是其中国的主要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员工。而该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设备来生产其调查期内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在缺乏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认定存在转运形式的规避行为。
对于马来西亚的公司,配合调查的公司仅占马来西亚对欧盟出口总量的20%~30%,该公司从2011年开始生产和出口自行车,调查未曾发现该公司存在转运的规避行为。对于其他公司,由于其未配合调查以及此前认定的贸易模式的变化,所以对于其他公司的出口认定为存在转运的规避行为。
对于斯里兰卡的公司,配合调查公司的出口占斯里兰卡对欧盟出口总量的69%,在配合调查的6家公司中,其中3家不存在转运的规避行为。对于其他公司,由于其未配合调查、或配合不充分,以及此前认定的贸易模式的变化,所以对于其他公司的出口认定为存在转运的规避行为。
对于突尼斯公司,配合调查公司的出口占突尼斯对欧盟出口的100%,调查未发现该公司存在来自中国的转运行为。
◎对于组装的规避行为,欧盟委员会分析了配合调查的每家公司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及其生产成本以确定是否存在通过组装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规避行为。
对于印度尼西亚,在配合调查的4家公司中,有3家公司来自中国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未达到最终组装产品总价值的60%,因此没有必要审查装配或完成过程中的增值是否大于生产成本的25%。所以,对于这3家公司不存在组装的规避行为;对于另外一家公司,由于其未提供可信的数据,所以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组装行为。
对于马来西亚配合调查的公司,欧盟委员会认定,该公司是2010年,也就是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增加以后才开始运营,该公司主要是针对欧盟市场,而且其使用的零部件也主要是从中国采购的,其在中国采购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占最终产品总价值的60%以上,而组装过程中产生的增值未超过生产成本的25%,因此满足了《反倾销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
对于斯里兰卡完全配合调查的3家公司,由于其从中国采购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未达到最终组装产品总价值的60%,因此没有必要审查装配或完成过程中的增值是否大于生产成本的25%。所以,这3家公司不存在组装的规避行为。
对于突尼斯,一家配合调查的公司在中国采购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占最终产品总价值的60%以上,而组装过程中产生的增值超过了生产成本的25%,因此不存在规避的组装行为。另一家配合调查的突尼斯公司从2006年开始运营,主要向欧盟出口,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也是从中国采购,并且持有其多数股权的股东是一家中国的自行车生产商,而其在中国采购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占最终产品总价值的60%以上,而组装过程中产生的增值未超过生产成本的25%,因此满足了《反倾销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的标准。
除规避反倾销税以外缺乏正当的理由或经济上的合理性
欧盟委员会认定,除了规避现行的反倾销税以外,转运和组装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或者经济上的合理性。除了反倾销税以外,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弥补通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或者突尼斯进行转运或者组装而产生的成本,尤其是运输和装卸方面的成本。
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被破坏
为了从数量和价格方面评估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进口的自行车是否破坏了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从数量上来说,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出口到欧盟的自行车数量是大幅增加的。从价格上来说,欧盟委员会比较了2005年期中复审时确定的损害消除水平与本次调查期内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认定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自行车存在明显的低价销售的情况。因此,欧盟委员会认定,从数量和价格上来说存在破坏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的情况。
倾销的证据
最后,根据《反倾销条例》第13条第1款,需要审查与以前调查中确定的正常价值相比是否存在倾销。以案例一为例,该案中贸易委员会以2005年的期中复审中确定的正常价值作为以前确定的正常价值。对于印度尼西亚,由于3家配合公司的生产确实是印度尼西亚本地的生产,所以只考虑未配合调查公司的出口,出口价格是根据欧盟贸易数据库Comext报告的调查期内印度尼西亚出口到欧盟的出口价格确定的。对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出口价格,也同样是按照上述方法确定的。同时,为使两种价格的比较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欧盟委员会对运输、保险和包装成本等进行了调整。最后,欧盟委员会通过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最终确定,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的出口均存在倾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欧盟委员会在进行裁决时,只有同时存在贸易模式的变化、规避行为(转运、组装等)、缺乏正当的理由或经济上的合理性、反倾销税的救济效果被破坏、存在倾销的证据时,才认定构成规避反倾销措施,并将原反倾销措施扩大适用于在第三国组装后的产品或存在转运的第三国的产品。
可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随着欧盟反规避调查力度的不断加强,反规避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贸易障碍。对此,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降低遭遇欧盟反规避调查的频率,并且在欧盟正式发起反规避调查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地应对欧盟的反规避调查,切实维护自身利益。
研究欧盟反规避规则,并运用规则为我所用
《欧盟反倾销条例》经过多年的修订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针对性强、操作性简单的反规避制度,对此我们应深入研究其反规避规则。以在第三国和欧盟境内的组装行为为例,欧盟委员会对规避行为的判定标准是“60%及以上的原材料是从被调查国家采购”,并且“组装或者加工最终产品的过程中发生的增值不超过生产成本的25%”。如果中国生产商在第三国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并计划未来将在第三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至欧盟时,企业就要严格控制在第三国加工的产品中使用的中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并且注意满足25%的增值测试的标准。
以上述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为例,对于印度尼西亚配合调查的4家公司中,有3家公司来自中国的原材料(自行车零部件)未达到最终组装产品总价值的60%,因此没有必要审查装配或完成过程中的增值是否大于生产成本的25%。所以,欧盟委员会认定对于这3家公司不存在组装的规避行为。
积极参与、配合欧盟的反规避调查,及时填写和提交调查问卷,接受实地核查,并提供必要的信息
在上述欧盟对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中,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生产商、出口商消极应对,不参与调查。在上述两起反规避调查中,无论是对原产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还是对中国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中国生产商、出口商均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没有一家企业积极参与欧盟的反规避调查,这也是导致调查结果对中国企业非常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欧盟反倾销条例》第18条第1款,如果利害关系方拒绝调查,或者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者严重妨碍调查,则欧盟委员会可以根据可获得事实做出肯定的或者否定的、临时的或者最终的裁决。而根据该条第5款,可获得的事实包括申诉方提供的信息,在可行的情况下,考虑到调查的期限,应参考从其他独立来源获得的可行信息,例如已公布的价格表、官方统计、关税返还或者从其他利害关系方获得的信息。而如果完全是根据申诉方提供的信息或者从其他独立来源获得的信息进行裁决,则最终的调查结果将完全掌握在欧盟委员会手中。
在上述欧盟对自行车的反规避调查中,由于参与合作的当事方数量较少,而中国企业更是完全未参与调查,因此欧盟委员会在裁决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从欧盟统计局数据库中所存储的外贸数据,并据此做出肯定性的裁决,将对原产于中国自行车的反倾销税延展至自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进口的涉案产品。
加强对反规避调查的预见性,建立和完善反规避调查的预警机制
研究欧盟发起的反规避调查可以发现,欧盟在对一种产品发起反规避调查后,后续很可能会对该产品再次发起反规避调查。以上述欧盟对自行车发起的反规避调查为例,2012年9月25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两年后,即2014年9月2日,又决定对中国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的反规避调查也是如此。2011年11月9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并经马来西亚转运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发起反规避调查;2012年5月23日,又对原产于中国,并经中国台湾和泰国转运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发起反规避调查;2013年4月9日,对原产于中国,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转运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发起调查,2013年12月17日,则对原产于中国、经轻微改变后出口到欧盟的玻璃纤维织物发起反规避调查。
由于反规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果,所以在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同时要加强对于反规避的预防。在对一种产品发起了反规避调查以后,国内生产企业更应该注意在海外的投资运营行为,以尽可能地避免可能发生的反规避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