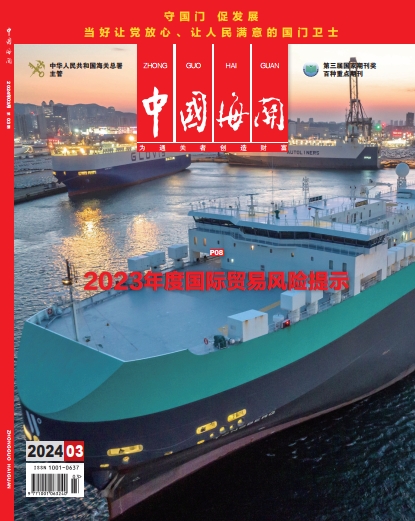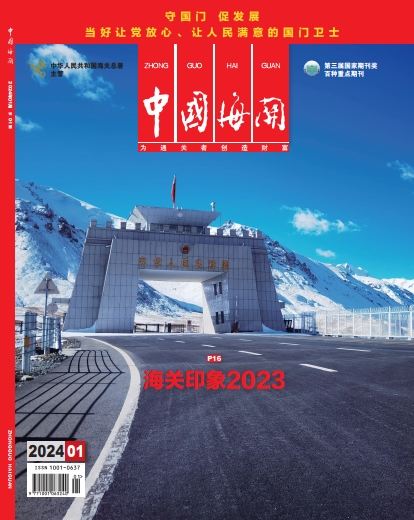CopyRight 2009-2020 © All Rights Reserved.版权所有: 中国海关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铜市火热 进口量价齐飞
作者:钟雁明
文 / 钟雁明
铜是最早被人类广泛应用的金属,对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虽不是最早使用铜的国家,但铸造的青铜器却达到了世界的顶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艺术成就,也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随着铁和瓷器的广泛应用,青铜器逐渐从礼器、兵器、工具、日常用品等诸多领域淡出,只在某些领域发挥余热,比如通行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铜钱,还有零星的铜镜。
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再次让铜焕发出勃勃生机,它被普遍应用到电气、电子、交通运输、冶金、建筑、艺术、能源石化、海洋产业和高科技等领域。如今,铜依然是世界上用量第三大的金属,仅次于铁和铝。从日用品到工业制造、建筑材料、电子科技、艺术美学领域以至于当下最热门的5G技术,均离不开铜的身影。
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持续增长
由于金属铜具有极佳的导电性能、优异的力学性能和抗疲劳抗腐蚀性能,在所有的金属中仅次于银,因此成为电气工业的“主角”,我国约四成以上的精炼铜都用于电力领域。电源系统中的发电机、电缆、断路器以及其他发电厂附属设备,电网系统中的高低压电线电缆、变电站等都需要铜。为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持续加大对电力工程的建设投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734亿元,2023年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9675亿元,电网工程完成投资5275亿元,电力行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对铜需求的高速增长。
此外,我国房地产行业、家电行业,以及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对铜的需求也持续快速增长。尽管我国精炼铜产量从2001年的152.3万吨猛增至2023年的1299万吨,并已经连续18年成为全球精炼铜第一大生产国,但仍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进口铜作为补充就成为必要的选择。
据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进口未锻轧的铜及铜材169.5万吨,此后进口持续增长,至2020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68.1万吨,后来受国际铜价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需求受到一定程度抑制,进口有所回落,连续3年进口在550万~600万吨之间徘徊,2024年前4个月进口181.3万吨,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7%,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
铜矿砂及再生铜进口增势强劲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我国把握发展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深入参与全球有色金属行业分工体系,不断壮大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一举成为世界有色金属第一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贸易大国,为世界有色金属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铜消费第一大国,从此连续22年保持榜首位置。2006年,我国精炼铜产量超过智利,成为全球铜第一大生产国,并保持至今。
我国铜矿资源储量相较于全球而言偏少,且大多分布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开发难度较大,运输成本相对较高。伴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铜矿的下游需求日益旺盛,我国铜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数量逐年攀升,2001年进口仅为225.5万吨,2013年进口量已经突破千万吨,达到1006.9万吨,2019年站上2000万吨的新台阶,2023年进口更是达到2752.9万吨的历史新纪录;2024年前4个月进口933.6万吨,继续保持6.9%的较快增长势头。
铜具有完全可回收性,与铜矿开采相比,再生铜的能源消耗远低于矿产原料,回收铜可节省大约85%的能源。2020年11月我国对符合特定标准的再生铜进口政策调整之后,经海关检验合格、达到国家规定环保标准的再生铜原料进口连续3年实现增长,从2020年的94.3万吨逐年增至2023年的198.6万吨,2024年前4个月进口78.3万吨,继续增长25%,有效地缓解了国内铜矿资源紧缺状况,在铜产业资源保障和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进口铜价节节攀升
作为大宗工业原材料的铜,被市场赋予了双重属性,即本身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和衍生的金融属性。金属铜常被市场称为“铜博士”,原因在于其价格走向通常被视为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铜价与全球制造业周期关系密切。当全球制造业开始补库存时,对于汽车、电子、家电等核心商品的需求往往带动铜价上涨,因此铜也被称为“周期之母”。与之相对应,我国进口铜价格同样呈现周期震荡波动的走势。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的年度均价从2001年的17127元/吨逐渐涨至2007年的阶段性高点54321元/吨,之后迅速回落至2009年的36078元/吨,2011年回升至58569元/吨后连续5年下跌,随后又开启新一轮升势,2021年进口均价已经突破6万元/吨大关,达到61303元/吨,比2016年的相对低点强劲上涨74.1%,此后连续3年保持在6万元/吨以上的高位,2024年前4个月进口均价达到62726万元/吨,继续上涨2.8%。
铜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均价与未锻轧铜及铜材的走势如出一辙,从2001年的3296元/吨涨至2011年的15579元/吨,然后逐渐回落至2016年8137元/吨的低点,2021年起连续3年保持在15000元/吨附近的高位,2024年前4个月进口均价达到15520万元/吨,继续上涨1.9%。再生铜原料进口均价亦跟随钢材价格起起落落,2024年前4个月进口均价达到53105万元/吨,上涨3.9%,达到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铜资源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
从全球范围来看,铜矿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鲁、北美洲的墨西哥和美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欧洲的俄罗斯和波兰、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亚洲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2023年全球铜资源储量排前十位国家的铜储量合计占全球铜资源储量的比重超过七成。我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西北地区的新疆,华东地区的江西、安徽,华北地区的内蒙古等,贫矿多、富矿少,资源禀赋不佳,接替资源不足,新增资源多在西藏等高寒、高海拔地区,开采难度较大。
与智利、秘鲁等铜资源大国相比,我国铜资源矿体小、品位低的劣势尤为明显。从储量规模看,我国储量规模仅居全球第九位,铜矿资源相对匮乏,与我国精炼铜生产与铜消费规模不相匹配。根据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GTT)提供的数据显示,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德国等国是近年世界未锻轧铜及铜材的最主要出口国。2023年,我国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智利、赞比亚、俄罗斯、韩国分别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107.7万吨、90.1万吨、47.8万吨、38.3万吨、27.1万吨,合计占同期我国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总量的56.5%。2024年前4个月,从以上5国合计进口105.6万吨,增长14.5%,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8.2%。
从铜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情况观察,2023年我国自智利、秘鲁、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墨西哥分别进口843.1万吨、724.7万吨、159万吨、142万吨、139.9万吨,合计占同期我国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总量的73%。2024年前4个月,从以上5国合计进口680.2万吨,继续增长9.6%。世界再生铜原料市场宽广,2023年我国自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其中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分别进口再生铜36.2万吨、28.6万吨、19.8万吨、15.4万吨,合计占同期我国进口再生铜总量的50.3%;2024年前4个月,从以上4国合计进口37.3万吨,继续增长22.3%。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都离不开有色金属,尤其是铜,未来对铜的需求仍将进一步走强,碳中和及人工智能浪潮是重要推动力。与全球铜矿资源相比,我国铜矿资源相对匮乏,在矿床规模、矿石品位和开采难度方面存在劣势,对海外资源依赖程度还在持续攀升。全球铜资源分布十分不均,近年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临历史性重构,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加剧,主要铜资源国通过调整资源税、关税以及矿产资源国有化、禁止初级产品出口、延伸产业链等手段实现产业链本土化,铜资源开发和铜原料出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海外资源开发风险不断抬升。今后我国仍需不断夯实资源保障基础,加大国内资源勘查,强化铜矿产资源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积极寻求外部铜矿资源,加强国内外再生铜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提升创新驱动能力,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合作,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高生产运营中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增强铜产业发展新动能。